本文作者为施爱东(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谣言学、科学哲学。著有《故事法则》《故事机变》《故事的无稽法则》《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等。本文节选自《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代后记,特此分享。

一、偶然选择了民间文学专业
我本科读的是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天气动力学专业,毕业于1989年。那一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正处在“工作分配”和“自主择业”的时代转换点上。我们的毕业论文没有举行答辩仪式,学校提前一个月就将我们这届学生派遣回各自生源地,我印象中连毕业酒都没喝,全班照了个毕业合影就离校了。
回到老家赣州地区,原定的用人单位说是今年不进人了,地区教育局直接把我的档案转回到我的生源地信丰县。县教育局从来没接受过我这种无对口专业的“名牌大学生”,压着不敢分配,说要听县里安排。等到9月份,其他毕业生都先后分配工作了,只有我还悬着。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直接去找县长黄际泉说理,县政府办公室一位刘姓副主任拦住我不让见县长,我拍着桌子跟他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最终还是没能见到县长,但这事很快轰动了小县城的朋友圈。据说县长知道这事后,指示教育局让我自己联系一个对口单位。我打听到县水利电力局还有编制,就申请去这个单位,县教育局在我的“派遣证”备注栏特别加了一行字:“分配水电局下属单位。”
信丰县水电局有8个下属单位,其中6个中型水库,我被分配到安西镇的上迳水库管委会。水库一般都在山沟沟里,管委会大多是安西镇人,每到周末就各回各家,只剩我一个人守着诺大一个水库。冬天枯水季节,水库发不了电,四野漆黑,时不时传出些野鸡和野兽的叫声,显得特别空寂,苍穹之下就只有我的房间亮着一盏煤油灯。孤独到绝望的恐惧感,时时逼着我坐到煤油灯前,捧起一本英语单词本,我也没有别的方法,只是死记硬背。
我在水库呆了不到半年,水电局人事秘书去世,局里想把我调到人秘股补缺,但是信不过我的文字水平,局长曾凤礼出题让我写了篇《假如我改行当秘书》,看完作文又不相信是我写的,副局长罗立章专门到我的母校信丰中学,找到高中部语文教研室主任陈明淦咨询。陈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但他非常肯定地对罗立章说:“这当然是施爱东自己写的。”
就这样,我在信丰县水电局人秘股做了三年秘书工作。那是我“混社会”的三年,我记得每到冬天,一下班,水电局的一班年轻人就会结伴到人秘股办公室生火盆、打扑克、喝水酒,有时喝多了,我就住在局里招待所,那种天地间只操心手里一把牌的感觉,还是很单纯很快乐的。当然,更多的业余时间是浪费在跟同学闲聊、闲吃、闲逛。县城的同学不分一中、二中,初中、高中,反正都是一个年龄段,大家组了一个“光棍协会”,我被推举为会长,有时还得负责组局找乐子。每天下班后,我和几个无聊透顶的同学就在县城各个街道浪荡二、三个小时,找娱乐项目,多数时候是找不到的,但也得浪到彻底绝望才回家。每天回到家我就后悔,天天骂自己,然后拿出单词本,背英语单词。
理科生做文秘工作,终究是不受信任的,1991年,江西省水利厅要在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办一个文秘专科班,局里决定派我去。让一个本科毕业生去进修专科班,我感到很屈辱,拒绝了这个机会。为了争口气,我决定考回中山大学读中文系“写作学”研究生,以证明自己能“写作”。
可惜的是,我落榜了。
铩羽而归的我自尊心受到重挫,自觉没脸继续呆在家乡,1992年我办了停薪留职,揣着积攒了三年的400多块钱,只身去了广东打工。经同学朱建军指点加介绍,我用虚构工作经历的手法,好不容易在番禺“隆辉工业村”找到工作,担任“生产部副主任”,月薪1200元,而我在江西的月薪是160元。我努力工作,虽然很快升职、加薪,但是累得骨瘦如柴。
经同学武少新劝说,我决定再次报考研究生。为了加大成功概率,这次我不敢赌气报考“写作学”,在招生目录中选了一个我在本科阶段就选修过的民间文学。
二、用“民间的方法”从事民间文学研究
1993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我考上了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后几年,我跟着导师叶春生几乎走遍了广东全省,跟他学会了跑田野、看风水,结交各种民间异人,还代他外出授课。我经常一个人背着书包在广东全省各地跑,每到一处就匆匆忙忙找图书馆,根据图书资料找点、找庙,东鳞西爪地问点风俗事象,拍些照片。其实对于如何使用和处理这些资料,心里并没有谱。
叶春生老师不主张用学院派的方法做民间文学研究,他的著述大多是民间知识的采录与整理,他早期的论文甚至很少注引文出处。我本来就是个理科生,没有写作规范的意识,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我比老师走得更远,硕士时期的文章就像天马行空,在处理不同民间文学异文的时候,往往凭自己的主观判断,综合整理出一个自认为比较全面、合理的新文本。叶老师很宽厚,也很少批评我,甚至动用他的个人关系,帮我把其中一些文章发表了。
硕士期间我还受到广东文坛领袖黄树森老师的深刻影响。我入学的时候,贾平凹《废都》正在大卖,黄老师来中山大学中文系做讲座,希望年轻人对此展开评论。我那时候根本没入行,还不会写论文,完全是凭个人理解和感想写了一篇《想做贾宝玉的男人们》,投给黄老师主持的《当代文坛报》,没想到黄老师很喜欢,特地把我和同学于爱成约到一家叫小观园的酒店喝早茶,从早上一直喝到下午,反复鼓励。此后两三年间,我在黄老师的指导下,非常勤奋地发表了一大批当代文学评论,包括后来成为畅销书的《点评金庸》。凭借黄老师的大力栽培和举荐,我和于爱成迅速成为黄老师所说的广东文坛第四代青年代表。
受到鼓励的我虽然隐约意识到自己这种率性的论文笔法似乎有些“不科学”,但我天真地以为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就该用民间文学的率性表达,“说出我们老百姓的真情实感”,甚至觉得用这种方法介入当代文学评论,还有点别开生面的新意思。
硕士期间,我不仅没有很好地掌握规范的写作技能,甚至刻意地让自己的文章与学院派规范写作保持一定距离。无论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还是民间文学调查,我都不拘一格,尽情挥洒我的学术想象,张扬自己的写作风格。这种学术进路直到我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时,才第一次受到答辩老师的批评。
我的硕士论文搜集整理了一大批非广东籍的外地人在广东如何化身为地方神灵的传说,论文标题原拟《外省人如何成为广东地方神灵》,叶老师觉得“民间”味不足,给我改成了《“外江佬”如何成为广东神》,答辩的时候,这个标题受到陈摩人老师的批评,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民间文学研究不是用民间方法做的文学研究。”
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叶春生老师的学术助手。我们师徒俩情同父子,他对我的厚爱和信任常常令我觉得“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我们合作主编了一部《广东民俗大典》,堪称广东民俗事项大全。叶老师有祖传堪舆绝学,社会交游极广,我自然也会跟着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学习堪舆技能,结识了一大堆三教九流。在我离开中山大学之前,叶老师门下的弟子基本都交给我管理,因此我也被同门师弟师妹们戏称为“令狐师兄”。他们大凡有什么不敢向叶老师提及的要求,无论合理不合理,只要我答应了,叶老师就没有不答应的。
事务性的工作多了,学术钻研就少了。忘了在一个什么场合,吴承学老师委婉地提醒我,大意是说,学术论文有论文的写作格式和学术语言,让我留意一下写作规范。其实吴老师的提醒与陈摩人老师的批评异曲同工,但我当时并没有把陈摩人老师的话当回事,吴老师一说,我就很当回事,这大概就是偶像和权威的力量吧。
1997年,黄天骥老师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了一个《易经》读书班,我一场不落听了一学年,黄老师的发散性思维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接着,吴承学老师又开了一个《论语》读书班,读书风格完全不一样。吴老师素以严谨、缜密著称,他的读书方法让我终身受益,我在吴老师这里真正感受到了学术的严肃和神圣。
大概是受到吴老师严谨学风的震慑,我那两年几乎写不出一篇论文。1998年我被广东省委组织部委派到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中学挂职副校长,期间对连山“瑶胞”做了一些田野调查。为了跟当地朋友搞好关系,我在连山喝醉好几次,也得到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可是,没有理论的指导,田野调查就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完了也就完了,我不知道如何将这些零散的调查材料化做有效的学术成果。
我一直坚持着下午跑步的习惯,住到中山大学园西区之后,发现吴承学老师也爱跑步,于是约跑。后来加入我们队伍的还有王坤和彭玉平。但是,四个人一起跑,水平参差不齐,大家都累,后来改成打羽毛球,再后来又改为快走,这样队员水平就比较平均了。我们从园西区出发,进中区,出北门,临近广州大桥再往回走。走一个小时,聊两项内容,学术和八卦。
我一度决心报考吴承学的博士,准备了一段时间,刚好黄修已、叶春生领衔的现代文学博士点批下来了,叶老师要求我继续攻读民间文学博士,中文系任命我做写作教研室主任,我只好打消了在古代文学领域继续深入的念头。
叶老师有个宏大愿景:续写中山大学民俗学的光荣历史,再造辉煌。可当时中山大学民俗学就只有我们师徒俩,于是大部分学术振兴的事务性工作都着落在我头上,好在那时我也年轻,有干劲。我们申请成立了一个“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先是编写内部使用的《民俗》小册子,后来创办了一本以书代刊的杂志《民俗学刊》(半年刊,共出八期)。再后来是联合历史系的王承文、人类学系的周大鸣、刘昭瑞等人,向教育部申报民俗学博士点,我负责资料搜集、申报书填写之类的基础性工作,最后由周大鸣老师润色上交。经过周老师的一番提升,我们的申报材料被列为全国第一,2003年与中央民族大学一起,成为继北京师范大学之后的第二批民俗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三、学术人生的三级台阶
我的博士论文原计划在华南民间信仰的话题上进一步深化,但是叶春生老师没同意,最终把“中山大学民俗学史”的课题交给了我。后续的学术经历证明,叶老师这个决策改变了我的学术命运。首先是因为学术史让我对整个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有利于学者个体在历史的、通盘的学术大格局中去寻找自己的学术定位;其次是让我有机会走近钟敬文先生,并且成为他招收的最后一个博士后,并且为我走进北京学术圈、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的大门提供了便利条件。
我的博士论文最后一个阶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钟先生片言只语的教诲,令我受益终身,我很快就将其中一部分整理成《汝奚不曰其为人也——钟敬文先生病中论学》发表在《民俗学刊》。比如钟先生认为,文章就是写给别人看的,不仅要可信,还要好读;文章不必多写,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他甚至以容观琼为例,说容观琼评教授的时候,“他只给我一篇论文,我说一篇就行,可以做教授,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必要十篇八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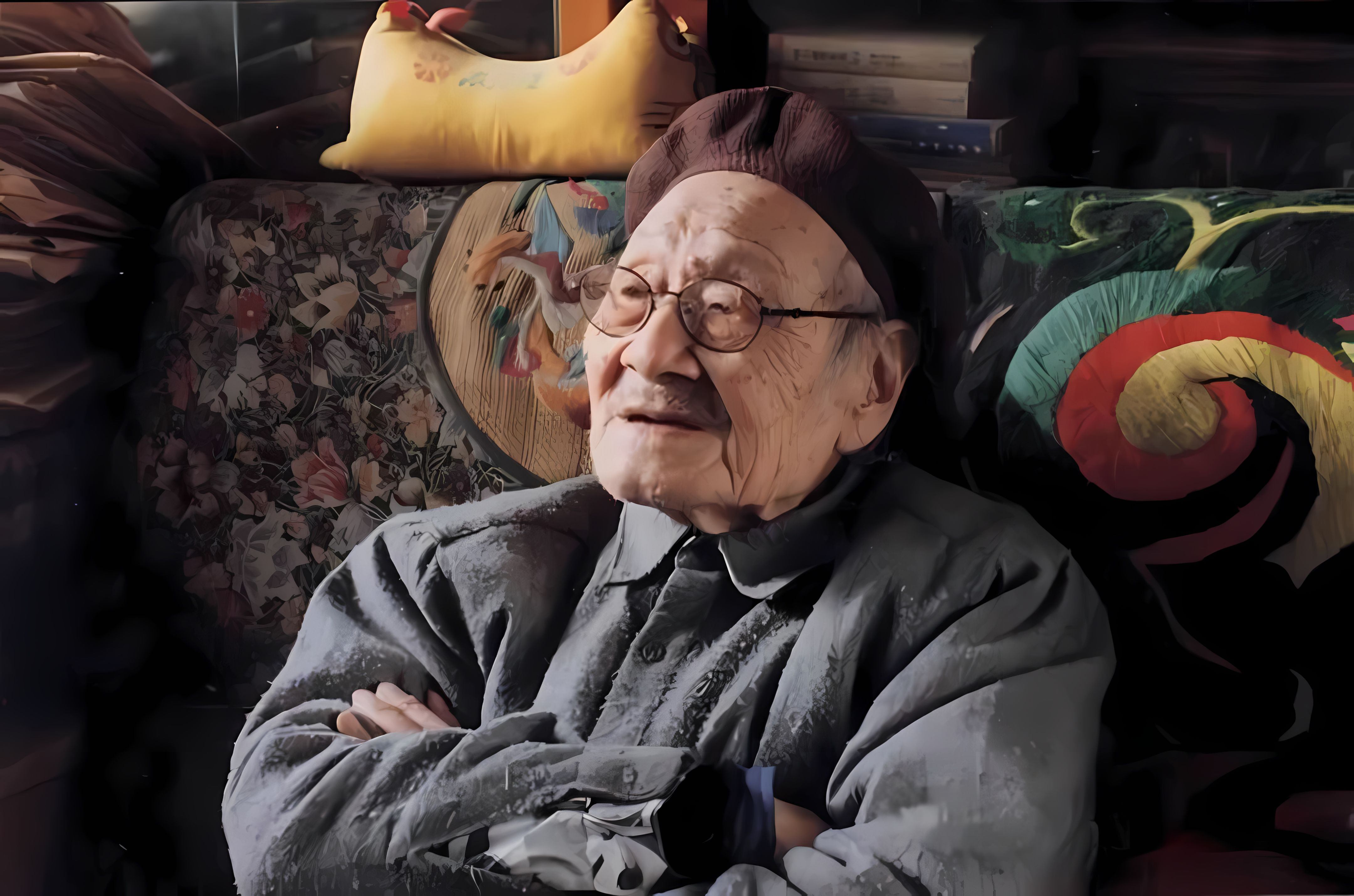
钟敬文先生
我还来不及博士后进站,钟敬文先生就仙逝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后工作是以钟敬文的名义进站,在刘魁立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刘魁立先生在许多领域都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尤以故事学为著,他曾经得到结构主义鼻祖普罗普的亲炙,在当今故事形态学领域可谓独步天下。拜师学艺当然是学老师的最强项,我决定把未来学术生命投向故事学领域。我相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比自己趴在地上摸索,不仅起点高得多,视野也会开阔得多。
这就是跟随名师治学的最大便利。
我的博士后工作是在学术史和故事学两个领域同时展开的,从事学术史研究是为了完成钟敬文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从事故事研究是为了习得刘魁立先生的学术菁华。前者的成果主要是博士后出站报告,也即2010年列入文学所学术文库出版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后者的主要成果是我在故事学领域的系列论文,后来我又按不同的研究进路将之整合成系列故事学论著出版。
博士后的三年,是我学术生命中最弥足珍贵的三年。那时候正当盛年,思维非常活跃,一经刘魁立先生的点拨,许多奔涌的感悟和构想,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就像散漫的水气逐渐凝结成水珠,滴落在笔端。一个学者只要写出了一篇好论文,他从此就跟过去不一样了,正应了钟敬文先生的那句名言:“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自从写出了《史诗叠加单元的结构及其功能——以<罗摩衍那·战斗篇>(季羡林译本)为中心的虚拟模型》,我就再也不是过去那个靠理解和感悟写文章的施爱东了。
如果说考上叶春生老师的研究生是我学术人生的第一级台阶、旁听吴承学老师的《论语》讲习是第二级台阶,那么,成为刘魁立先生的博士后是我的第三级台阶。叶春生老师把我领进了民间文学的大门,吴承学老师激发了我规范写作的学术自觉,刘魁立先生点燃了我理论思考的激情,唤起我理科出身的逻辑思维优势,让我获得了真切的学术自信。
四、参与创办“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1年12月,叶春生老师在中山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钟敬文先生百岁寿庆暨‘现代化与民俗文化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会务负责人,向叶老师申请到一点经费,晚上约了几位青年学者到广州“粥城”吃夜宵、喝啤酒。回到宾馆,大家意犹未尽,坐在会务组朱钢的房间继续聊。一天会议下来,我们都特别厌倦老一辈民俗学者关起门来“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做派,多次学术会议上积聚的“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加上适度的酒精作用,我和陈泳超不约而同地提议“造反吧,别陪老人家玩了”,来自台湾的钟宗宪和一向温和的萧放也表示了赞同。当时我们手上都没有经费,约定分头发动青年学者,组一个旨在提倡正常学术批评的学术沙龙,每年至少碰一次头,大家各自掏钱与会,AA制,不给主办者造成任何经费压力。
陈泳超回到北京之后,首先联络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吕微,得到吕微热烈响应。2002年7月,“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大会的多数时间都在讨论学会班子的改选问题,仅有的一点学术讨论时间,也被一些老同志的长篇大论给占去了,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数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只给两三分钟的发言时间,这种风气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揭竿的机会来了。当晚由山东大学叶涛做东,吕微、陈建宪、萧放、叶涛、陈泳超、刘晓春、施爱东七位青年学者(加上缺席会议的台湾学者钟宗宪,一共八位发起人)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找个了茶馆,召开了一次梁山会议,议定组建一个以学术批评为宗旨的青年学术团体。
我们原本打算建一个公共邮箱,方便大家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交流。后来陈泳超找到精通IT的硕士生陈永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BBS下面建了一个分论坛,起名“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有了根据地之后,大家分头联络民间文化界的青年朋友,邀请加盟“论坛”,刘宗迪就是被我们拉进“论坛”的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一大批早就憋着一股不平之气的青年民俗学者,聚集在“论坛”,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尽情地批判不良学风,恣意嘲讽前辈高论,拒绝自吹,也尽量不捧闲场。
“论坛”网页是2002年9月22日开始投入运行的,其时正值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入站,脱离了家室之累,一人闲在北京,时间非常富裕。白天到刘魁立先生的办公室喝茶聊天,有时帮着刘老师打打字,晚上回到宿舍,就泡在“论坛”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民俗学者笔墨往来,讨论各种关于民间文化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中的很多想法,都是在这些往复问答和论辩中逐渐形成的。
很快我和陈泳超就发现“论坛”中有一些奇怪的马甲,他们的用词习惯、言语方式跟我们有着明显的差别,比如言词客气、落笔稳重、标点符号一丝不苟,等等,经过一番比较分析,我们判断他们分别是刘魁立、刘锡诚、陶立璠等前辈民俗学者,但是我们并不戳穿,假装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有时还跟他们开一些善意的玩笑。后来的结果正如陈泳超说的:“慢慢的,我们发现那些老先生也逐渐放下以前的架子,变得越来越和蔼,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和谐,大家真的形成了一个比较平等交流的学术共同体。”
为了吸引人气,烧旺“论坛”,我和陈泳超、刘宗迪、钟宗宪还注册了多个马甲,不断挑起话题,相互插科打诨、斗嘴打趣,到处煽风点火,把“论坛”烧得热火朝天,很快就将之办成了“青年中国民俗学会”,从此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的“黄金时代”(吕微语)。
那时候,中国的青年民俗学者要是没在“论坛”上有个马甲,甚至都不大好意思说自己是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从业者。我们举办的年度“沙龙”很快就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民俗学最大型的“学术年会”,报名参会的人数甚至超过同一年度由中国民俗学会官方举办的学术会议。

中国民俗学会是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的“革命”对象,而当时的学会理事长正是刘魁立先生。在现实世界中我是他谦恭的学生,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我却是与之辩难的难缠对手。白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左右,我和林继富几乎每天都呆在刘先生的办公室,面对面地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刘先生从不午睡,我们中午在白兰餐厅喝两瓶啤酒,没老没少地胡吹猛侃,下午回到办公室继续干活,我们很少谈及“论坛”,我也装着不知道他有一件唤做“聪明的糊涂虫”的隐身衣。到了晚上,我就装疯卖傻地绕着圈子跟“聪明的糊涂虫”捉迷藏,可惜的是刘先生打字太慢,网上等他回一段话得等上好几分钟,后来我们就不爱跟他玩了。
五、栖身文学研究所
我对于自己能够留在中山大学任教非常满意,从未想过离开,直到我来了北京。我申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我的师母张玉娥老师对叶春生老师说:“不能让施爱东去北京,他去了就不会回来了。”我说:“我不会离开中山大学。”我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就像所有恋人在热恋时说的话一样。
进京之后,我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的学术氛围。别说隔三岔五的学术会议,五花八门的学术沙龙,即便是三五同业好友,在“小辣椒”这样的路边小店一碟花生二瓶啤酒几样小菜,聊聊学术八卦,说说新近想法,亦能引发思绪纷飞,碰撞出令人惊奇的思想火花,其中乐趣,是我在广州很难体会得到的。
我已经想不起到底是在哪次聚会上,时任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满脸大胡子,被我们戏称为“经略府提辖鲁智深”的吕微,向我提出了欢迎加盟民间文学研究室的邀请,但我当时虽然深爱北京,向往文学研究所,无奈曾经答应过叶春生老师不会离开中山大学,只好委婉地拒绝了。不过吕微撂下一句话,给我留了条后路:“什么时候想通了,随时给我电话。”类似的话他说过两次,我很心动,但始终不敢答应。
印象中是2004年5月的某一天,我在中山大学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突然觉得大为释怀,我再也不用背负“不会离开中山大学”的心理包袱了,我满心欢喜地给吕微打了个长途电话,问他:“民间室还有我的位置吗?”吕微那头显得也有些兴奋,他说刚好过两天所里要讨论人事问题,叫我赶紧给一份简历,他会事先跟杨义和老包说说,到时再交到会上讨论。大约才过了两三天,吕微电话告诉我非常顺利,文学所已经同意接受我的调动申请。
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为了防止被中山大学挽留和劝阻,我没把消息告诉任何人,悄悄北上,以躲避是非。2004年9月本该是我博士后出站的时间,我正在焦虑如何向中山大学提出调动申请,那天清晨7点左右,我还没起床,突然接到叶春生老师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今天早上遇到黄天骥老师,他主动说前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赶紧回来吧,最近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回来一起做。”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泪如雨下,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跟叶老师说的,总之是语辞委婉而态度坚决地表达了想留在北京的意思。叶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我的哽咽,他没有多劝,只是让我从家庭和收入等角度再考虑考虑,别急着做决定。大概他早已预感到我会留在北京了。
既然已经说开了,我就索性回到广州,正式向中文系主任欧阳光提出调动申请。欧阳老师非常惊讶,他说:“系里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舍得吗?能不能给我个面子,缓一缓再说?”我说好的。但我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广州,既然有了借口,是他们先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就把借口用足,决不松口。
为了能留在北京,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直拖着不肯办理出站。我在家乡做过人事秘书,知道一旦出站回到广州,再想进京,那就千难万难了。2005年春节,欧阳老师特地到家里来拜年,告诉我中文系准备派我去韩国任教一年,可以增收20万元。我当时说了一句让他有点难堪的话:“我一定要去北京,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我对自己的这句对答很满意,在不同场合说过好几次。在春节的师门晚宴上,从事房地产的师弟朱培坤搂着我的肩膀吐着一嘴酒气说:“师兄,你别走,我资助你一千万,你给我把中山大学民俗学事业振兴起来。”我笑着回答说:“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
欧阳老师始终没答应放我走,北京师范大学这边又总催着我出站。2005年初,我到博士后管理办公室打听政策,得知如果中山大学人事处同意我出站不回去,他们就可以将我直接派遣到文学研究所。我回到中山大学一打听,学校的人事政策非常开明,入职要求虽高,离职却很容易,只要本人提出申请,人事处就可以放行。于是我自己写了一份证明,直接绕过中文系,在人事处盖了个章,马上飞到北京,立即办理出站手续,直接以出站博士后的名义在文学研究所报到了,当时接待我的两位人事处干部是郭一涛、夏晶晶,她们的热情和笑容让我如沐春风,一下就打消了我入职前的各种不安和顾虑。
我2005年5月入职文学所,但是档案和工资关系都还在中山大学,每次节庆发工会福利的时候,全所就我一人没有。安德明很为我抱不平,找到工会副主席郭林,得知是因为我的工资关系还没转过来,没法扣交工会会费,不能享受工会福利。回到室里,安德明就像自己做错什么似的,执意想要把他的工会福利转送给我。类似的这种温暖故事还有很多。我在民间文学研究室的前后两任室主任吕微、安德明,都很温柔敦厚,从不强人所难,我在文学所这些年,自由自在,如鱼得水。
我出站的时候就办好了户口迁移,夏晶晶给我办了工作证,郭一涛为我争取了临时住房,我基本上没什么后顾之忧,每周来文学所上班,用文学所的名义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同时,我还领着中山大学的高工资(当时我在中山大学的月工资扣除奖金是3800元,后来在社科院的月工资是1700元)。中山大学这边,据说是学校对中文系进行年度财务审核时发现问题,要求中文系尽快处理好我的人事归属问题,于是系党总支书记丘国新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在北京这边安顿好没有,然后说:“要是安顿好了,就把工资关系也转过去吧。”我这才恋恋不舍地把工资关系转出了中山大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创新工程之前,每周返所日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签到制,时间比较自由,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大约在我入职文学所三个月后的某个返所日,由于我一般到得比较早,那段时间基本都是我开门、打开水,这天一拧钥匙发现锁已经开了,我心里一惊,开门就看到会议桌前坐着一位陌生女同志,正在写什么东西。她吃惊地看着我,我也吃惊地看着她,我们在会议桌前默默地相对坐了好一会,她试探着问:“请问你是新来的吗?”我说是,她说:“我叫张田英,我也是民间室的。不过,我很快就退休了。”我马上表示了不相信,我觉得她应该跟我差不多年龄,怎么就快退休了?出于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我一直坐在室里不敢离开,直到户晓辉进来。
摸爬滚打了又十年,直到我快40岁的时候,才明确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人生理念:尽量做好份内的本职工作,认真做好自己喜欢的工作,坚持“减法原则”,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有限的事业上,决不给自己加戏,不折腾自己。





